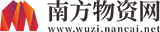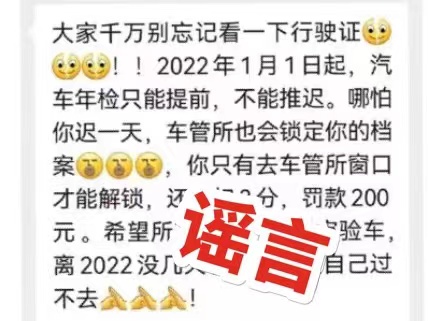“喂,你说,小王子会不会曾经游历过月球,甚至在月球上小住过一段时间?”她面向我趴在我的课桌上,双手托着下巴说到。
我把注意力从窗外的蓝天中收回,看着她看向我的眼睛:“怎么会突然把小王子和月球想到一起呢?”
 (资料图)
(资料图)
“因为,会很美吧。”
“美……吗?”
“你想啊,在月球上没有大气层,那就意味着放眼望去可以看见无数繁星和缥缈的银河。在星空的照耀下,地球成为了巨大的幕布缓缓升起,一片深邃的蔚蓝上飘浮着几缕波澜的洁白。在星河萦绕,蓝白笼罩的天地间,在灰白色的沙砾中,小王子的玫瑰花绽放出一抹艳红,在太阳照不到的背面摇曳着唯一的色彩,在太阳直射的极昼反射出最耀眼的光辉。”说着便想拿起纸和笔画出她心中那美丽的场景,“真的很美不是吗?”
“我知道了,知道了。”我边回应着边阻止了她想要创作的欲望,因为身处高中,一张干净的草稿纸实属可贵,“我能想象出来哦,真的。确实很美。”
“对吧,而且那里很适合小王子。那里不大不小,能看日落,更能看地球的轮廓渐渐的消失。我想,在小王子接触到那些无趣的大人后,在来到地球以前,路过这颗名为月亮的星球时,一定也曾幻想过在这里定居吧……”她将自己托着下巴的双手放平在桌子上,看着我刚刚一直盯着的天空,“好想……去趟月球。”
她的双睑似乎沉下去了一丝,相应的,她双眸的光似乎也减去了一丝。我并没有接着她抛来的话题,只是继续看着我刚刚注视着的天空——白天里月亮那淡淡的痕迹。我们俩就这么望着远方的天空。
我和她相识并不久,并非是小学或是初中就认识的同学。即使身处高一的同一个班,我们也是那种上下楼梯时擦肩而过都不会互相点头打招呼的关系。而现在,她是我在班中乃至整个高中时期唯一的朋友,我想必也是对于她来说这样的一个存在,但按照她自己的话来说,我是她自出生以来唯一的朋友。或许多少存在了一点夸张的成分,但是就我对她的了解来说应该也大差不差。至于我,并不清楚所谓唯一的朋友的概念,也并摸不清楚她在我心中的位置。但如今十几年过去,每当心中的压抑越过了极限,无力感充斥着全身,浑浑噩噩瘫倒在床上时,总会不由自主的在脑海中浮现出她的声音,她的脸庞,她的笑容,以及她那愿意听我诉说一切的耳骨与心。
至于我们怎么互相成为的朋友,这段记忆已经多少有些模糊了。我是那种不参与任何事与活动,不喜欢人多的环境,不喜欢吵吵闹闹的哗众取宠,放学时就一个人离开教室,老师上课都不会提问的那种人。而且在当今这个信息化的时代我甚至很少使用互联网,这种莫名其妙的特性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不方便,但我也真正的害怕自己变成一个浮躁且聒噪的一个人。所以,我在班级这个环境中并不是一个适合做朋友的人。
也许她比我更甚。细细想来,她的容貌在当时绝对算的上是一个美人。在那个荷尔蒙迸发的时代,这种面容姣好的女生应该很受欢迎才是,但她却说:“我一直没有什么朋友,连关系能称之好的人都屈指可数哦。”我努力的在脑海中忆起她的形象,当时我是坐在她的侧后方,她的马尾高高扎起,白皙的后颈若隐若现。密长的睫毛跟随着眼睛的闪烁频频的抖动着,如玉般的双手一边拨弄着一侧的发梢,另一侧用纤细的指尖奋笔疾书。但最为印象深刻的更当属那黑洞般的双眸,一颦一笑似乎都隐藏在这双如湖一般的眼睛之中。当然,我实在没见过她的笑容。
但她依旧属于被孤立的一个人。因为在她的周围总是散发着一种让人难以接近的氛围,而那种氛围常常具化在她那美丽的面庞中,藏匿在深邃的眼眸里。若是要给这种让人难以接近的氛围冠以一个名词,我想“阴郁”一词应最为合适。既不是阴沉,也不是抑郁,而是一种让人难以捉摸的“阴郁”。所以说,班里曾流传过她是抑郁症患者时,我只是一笑而过。而对此传闻,她更是不闻不问,犹如这些流言并非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像是自己的灵魂已然置之身外,在用第三人称视角操控着自己的肉体一般。但正因为她所透露出的氛围,也让她能躲开女生中不抱团所产生的欺凌。她只是在看着书,我想。
很难找到我们的契合之处,或许在他人看来我们都属于沉闷不出声,独来独往的自己看书的阴沉性格,是实实在在的一类人。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我和她之间的差别并不比小于我和那些在人潮中呼风唤雨的人的差别。因为我是实实在在的喜欢一个人独处,而她似乎深深沉浸在没有知音的痛苦之中,虽说知音难觅,但她甚至找不到一个普普通通的朋友。想必是因为这样,她才会渐渐的依附于我,但是好像永远是我在向她诉说些什么,如此看来,至始至终我都并没有了解过她,至始至终她也只不过是把我当做“可以说话的人”来看待。但我又是为何会不停的向她诉说,以至于到了现在还会时不时想起她的音容笑貌?现在的我只是现在的我,只能用旁观者的身份观察着记忆中的她与我,但是为什么,终究不得而知。能想起来的我们之间的共性,大概只有不用互联网。
那天我忘了带小说,只能坐在位置上转着笔,百无聊赖地看着没有一丝云迹的天空,忍着眼睛被光刺激的酸痛寻找着在湛蓝深空中那若隐若现的月球的轮廓。看了一会儿,不得不把头转了回来,用纸巾擦拭着眼中被刺激出的泪水,再转头看向教室发现房间如此黯淡。我去卫生间用凉水轻轻拍打这自己的眼睛,回到教室看见一本书静静的躺在讲台上——《小王子》
在讲台上,那应该是没人要的吧,我在心里想着。然后后退了两步,看了看下午的课表。
下节是自习课啊,那就……
一边想着,一边拿起了讲台上的那本《小王子》回到了座位。平时书看的不少,再加上本身也是一部不长的童话,所以我一节课很快的看完了这本书,把它摞在了我旁边高高的一堆教科书上。然后继续看着丝毫没有变化的天色,转着丝毫没有变化的笔。
“那个,请问,这本书是从哪拿的吗?”
我顺着声音转过头,看见她站在我的课桌旁,翻着我放在那堆半人高的教材顶部放着的《小王子》。
“从讲台上拿的,忘了带小说,想着没人要正好我这节自习看来着。”
“喜欢看书?”
“推理和科幻看得多一些。希区柯克,东野圭吾,阿西莫夫,刘慈欣的书我都挺喜欢。”
“这个……看完了吗?”她拿起书举在胸前,“感觉怎么样。”
“很喜欢,一口气读完了。”我面无表情的回应着,“我挺喜欢小王子旅行前的生活。”
“嗯嗯,这本书是我的哦。”她到我前面的空位上坐了下来,“喜欢小王子在初始星球的生活吗?”
“嗯,可以一天看44次日落,有花与星空陪着。虽然说可能会失去很多,但寂寞总有寂寞所独有的美丽吧。”
“喂,你说,小王子会不会曾经游历过月球,甚至在月球上小住过一段时间?”
……
第二天,我的桌子上多出了一本书,于是那本书变成了我继《安徒生童话》和《小王子》后读过的第三本童话——《银河铁道之夜》
现在想来,这些已经是十几年前的往事了,久远的高中场景历历在目得如此真实而清晰让我感到很惊讶。而立之年已过,不惑之年也在前面向我轻轻挥手,高中那段青春所渲染的墨迹被时间的流水层层冲淡,她连同青春一起流逝在那个名为记忆的永恒不变的花园中了。后来的大学也曾有过三五好友,也曾有过几次快餐般的恋爱,但他们姓名甚至与我一起所经历的往事已然想不起来了。而唯独她的的一切,她与我的三言两语都深深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或许,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在等待着与她再次相遇,然后如同在高中一样相互交换着自己喜欢的书,聊着喜欢的音乐,再时不时的向她倾诉些什么。
但为什么她从未向我倾诉过什么,当时的并不喜欢和他人交际的我又是为什么依附于她。实在让人难以费解。当下的我,已经辞去了工作,想来也是讽刺,高中从来不用互联网的我再大学学起了互联网的相关专业,又很好运的迎上了互联网与自媒体的风口浪尖,在短短几年积攒了一些积蓄。说到底,我依旧打心底对互联网上的混乱戾气充满芥蒂,于是在存款能够我轻松生活一段时间的情况下回到了老家,在家中看书,在街边散步,偶尔会计划着出去旅行。
我们以《小王子》的事情为契机,关系逐渐亲密了起来。在学校这个环境中也常常相处在一起,班里会传来一些流言蜚语,不过我们也从未在意。因为我们彼此十分清楚:“对方可能永远不会有那种感情。”一直直到毕业,乃至毕业以后,我们也没有交换过任何联系方式,即使在高中的关系再如何亲密,在毕业之后理所当然的没有任何交流,于是互相淡漠于彼此的人海里。她也许在等着我的联系,但当值青春稚气,即使有些思念也坚定着绝不联系,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正确与否,唯一知道的只有她可能永远成为回忆的事实,至少在我的世界里,她永远是以十七岁存在着。
“那本书,看完了吗?”没过几天,她又走到了我的身边,问。
“看完了。”我说着边从书包里掏出了《银河铁道之夜》递给她,“很好看,谢谢你。”
即使是这简单的谈话,就已经让周围的人呈现着诧异的气息,一开始我还感到有一丝不快,但慢慢发现,这种诧异感只是针对于她,和我鲜少有所关联,多少松了口气。
“喜欢吗?要不要再看一本呢?”她挥了挥拿在手上的书。
等她停下手中的摇摆,我才看清了这本书的名字——《爱丽丝梦游仙境》
“这么喜欢童话?”
“嗯嗯。”她轻轻摇了摇头,“我从来不挑书的。怎么了?不喜欢童话?”
“那到不至于,虽然谈不上特别喜欢,但还是挺有意思的。”
“好嘛。”
“对了。”我低下头翻找着我塞得满满当当的桌肚,她有些不解得微微歪头。
“那么,礼尚往来。”我拿出两本书放在她面前,“看过吗?这些。”
《黑猫》和《白垩纪往事》
“没有,我看的大多都是文学性的书,其他的就科普性的百科全书看的多一些。”
“我还以为你只看童话你?”我打趣到。
“怎么会。”她转瞬即逝的笑了一下。
在接下来的很长时间里,我们互相借阅着自己喜爱的书籍。借她之手,我看了《窄门》《百年孤独》《人间失格》《德米安》这些我曾未听闻过的书籍,相对的,她也读过了在我手中的《江户川乱步集》和《三体》。我们会在教室里一起阅读着《初恋》《山月记》《西西弗神话》《变形记》,会在为数不多的休息日一起到她家开的图书馆里探索着《草木塔》《坑夫》《地下室手记》《弗兰肯斯坦》里的世界,时不时在《基地》中想着银河帝国,即使是《福尔摩斯》也会一起津津乐道。但无论如何,也只有我会向她倾诉,明明是她想要依附于我,但渐渐的确实我难以离开她。
我也曾直截了当的问过她,为什么不愿意向我敞开心扉,为什么只有她在慢慢了解我的全部而我却一直对她一无所知。
“这个,你听我说。如你所知,我家是开图书馆的。正因为如此,我从小在那里长大,很少与外界接触,与我朝夕相处的是有那一座座需要抬头仰望的暑假和那些排列得密密麻麻的的书本。我一本又本的不停地啃噬着我家中那似乎无穷无尽的书本,对外面世界的一切渐渐的从无知到好奇再到无感。因为我感觉这里这么多书,里面的这么多故事已经能够囊括外面所有的世界了,说不定外面真实的世界并不比书中描绘的一切有趣,现在看来……果真如此吧。”
她垂下双眸,继续轻轻得说着:“所以等我好吗?等到我真正能对外界敞开心扉的那一天。”
但说到底,这些也只不过是回忆罢了。虽然我一遍又一遍的说着她一直在我的心中与回忆里未曾消散,但我现在并不想着与她重逢,因为我并不知道应该报以怎样的心绪再见她,更不知道她现在的一切又是怎么样,因为在我内心深处,她的形象已定格在了十七岁。
我继续延续着自己生活的轨道,人生的列车不变的前行着。我很久以前就做好了这次旅行的计划,现在我已经趁着夜色到达了候机室入口的安检处。
我如今也多多少少坐过十几次的飞机,对于机场这一存在是相当的喜爱,机场入口笔直宽阔的接送车道,高高的指挥塔,空旷高耸的候机室,外面平垠的跑道上缓缓闪烁着五彩的指示灯,这一切都让人的内心无比平静。这次我旅行的目的地,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岛,已经很久不再想念这种寂寥无人的地方了……
几个小时悄然过去,飞机平稳着落,我又匆匆坐上了最后一班轮渡,又摇晃了半个小时,终于抵达了我想抵达的岛屿,浪迹飞散于船尾,前方模糊的墨绿山岳慢慢逼近,波涛与礁石在岸边沙沙作响。
码头一盏明亮的灯光摇曳着等待轮渡的到来,与我同船的游客刚刚下船边一哄而散,向着岸边狭长的夜市与山顶的民俗走去。
不知怎得,没吃晚饭的我依旧没有进食的欲望,既不想混迹在拥挤的夜市,也不想到民宿中无所事事。于是向着远离陆地的那侧岸边走。海风带来的清凉里携着盐味与潮湿,一侧是无边的海水,另一侧是铺满植被的山丘,在这之间行走,似乎这条环岛的公路在永远得向前延申,又或是我一直在这里原地踏步。天空中伶仃的云迹,两边的山岭与海洋,永远都不会因为我向前的脚步发生变化。背上的汗水不知不觉浸湿了衬衫,脚走得也有些酸痛了。而眼前那座灯塔渐渐的由细小变得高大,证实着我的移动,更证实着我在这片天地的存在。
直到一条细长通往海面中央的由钢筋水泥灌筑的海桥全然暴露在我的视野之中,我才停下脚步,深深呼吸着咸咸的海风,看着一路皎白的路灯拥簇下的灯塔矗立在海桥的尽头。我闭上双眼,向灯塔走去,沐浴着灯光的照耀。
灯塔上庞大的灯周而复始的扫过我紧闭的双眼,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想起小学时的我还会经常把自己蒙在被窝里打开着手电筒照着,因为这对我来说有一种到达了某个陌生而美好的世界一样的幸福感。可能是因为那时的每次旅行都是父母的奖赏,在火车卧铺上路过一站又一站时,站内的灯光都会打到我的脸上,让我不停的期待着明天的到来。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我的脑海中突然想起这句诗。交界明月与灯塔的灯光交相辉映,洒在海面上波光粼粼,巨大的月亮圆的喜人。回过神来已经走到了灯塔下方,这是才发觉灯塔是如此的粗壮高大,微风掀起波涛,拍打在灯塔钉在的六边形的人造半岛。我不知为什么,神使鬼差的敲响了面前锈迹斑斑的铁门。
怎么可能会有人呢?不说这么晚的时间,这里到底也没有人驻守也不一定。
我转过身,准备离开这里,去夜市买瓶啤酒降温。
身后突然传来铁门被推开的厚重杂音。我好奇的转过头去,随后呆滞在了原地,而对方的反应似乎比我从容,但也说不上比我好到哪去。
她的脸上很少见到被岁月侵蚀的痕迹,但仔细观察,还是能看见她眼角那淡淡的细纹。十几年过去,她看起来消瘦很多,但完全没有那种让人不适的骨感 反而更加高挑。面庞依旧美丽且让人难以靠近,但那份阻隔已然从“阴郁”变成了“无”。没错,“无”,是她澄澈双眼渗透到面庞充斥到全身的氛围。
我们就这样呆滞地看着对方,在这一分钟,世间失去了声音与颜色。我不知该如何开口,直到她率先打破了这份沉静:“还站着干嘛?进来坐坐?”
就如这失去彼此的十几年并不存在一样。
我们攀登着灯塔,两个人依旧一言不发,只有两人在螺旋的铁质阶梯上悦耳的噪音。直到来到了顶楼。
很简单的内饰,一张小床,几副书架,卫生间静静地呆在一旁在书架的背面,有一个能用来做一些简单饭菜的灶台。最引人瞩目的是一扇略大的窗口,窗帘无声的摆在两侧,月亮正好位于窗户的正中间,似乎月球就是为了镶嵌于其中而存在,在月光的直射下,一朵红艳的玫瑰,倔强得随着海风摇摆着,绽开着。
“欢迎光临。你变化真大,我差点没认出你。”
“十几年了都,高中时代早就不见了啊。想我们当初……”
她摇了摇头,打断了我的话语:“当初怎么样都无所谓的,也不曾后悔过任何事,这一切的发展应该都是最优解了。”
我看着她,顿了一会:“什么时候来的。”
“大学毕业。”
“怎么样?”
“很好啊,这里有我一个人的人海,看着鲜花次次盛开,还能离月球这么近。”她望着窗外的明月,“月光是海的梦境,在这里也算是满足我去月球的愿望了。”
我没有接话。她就犹如小王子,从某个小星球来到地球,但是她定居在了月球。
“现在依然不用互联网?”
“怎么会。”我苦笑着,“就因为互联网才让我有闲情雅致出现在这里。不过我也因此辞去了工作,不再有就是。”
“可还爱看书?”
“被你影响,喜欢过一段时间纯文学,现在偶尔看看人物传记,年龄大了慢慢看不下去书了。”
“我倒是还在一直看。”
“果然没什么变化嘛。”
之后又陷入了一阵沉默。
“喂,你知道吗,高中毕业之后我依旧没有过朋友,这样看来,你可能是我一生中唯一的朋友了。但我应该从来不是你的唯一吧。”她微笑着说,眼角的细纹甚是好看。
“是有一些朋友,也有过几次快餐式的恋爱。但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记得的只有你才是。”
她又在微微笑着:“要不喝点啤酒?冰箱里又冻了好几天的。”
“乐意至极。”
我们拿着几罐冰透了的啤酒,爬上了灯塔的最高处。身后的瞭望灯忽闪忽闪,我眺望着远方的海面,她依旧盯着月球。海风吹拂着她身着的白色连衣裙,挽起着她披在肩上的长发。我们一罐接着一罐的喝着啤酒,依旧没有说话。身边的啤酒罐堆了一堆,我咽下最后一口已经恢复常温了的啤酒,也顺带咽下了我堵在喉咙里想说的一大堆话。我放下啤酒罐,整理了一下外套——我知道我该走了。我转身看向她,发现她正看着我,并轻轻点了点头。
我们仍旧默不作声的顺着螺旋阶梯向下走着,仍旧只有走在铁阶梯上那悦耳的噪音。
我用力的推开锈迹斑斑的铁门,一阵海风吹乱了我的头发。我迈出了灯塔,并没有回头。
“喂,等一下。”她平淡的喊住我,“想来,你就是我的远行吧,请让我在你那里的故事等着我,等我回来。”
我回头看着她,使劲的点了点头。
那晚在民俗睡觉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睁开眼发现我居然身处在月球上,旁边一个蓝白相间的巨大星球慢慢得升起,轮廓渐渐的清晰,头顶繁星闪烁,日光熠熠生辉。我看向前方,发现前方有一朵盛开的玫瑰,明亮的红光彰显着自己的生命力。我不自觉的迈开了双腿,追逐着那朵玫瑰。但那朵玫瑰好像一直向前移动着,又或者我又在一直原地踏步,那支玫瑰永远与我有着那一段恒定的距离。但我不断奔跑着,在月球上追逐着这朵玫瑰……
关键词: